SERVICE PHONE
13988889999发布时间:2025-11-19 21:39:06 点击量:
哈希游戏,哈希游戏官网,哈希游戏平台,哈希娱乐/哈希游戏作为一种新兴的区块链应用,它巧妙地结合了加密技术与娱乐,为玩家提供了全新的体验。BET哈希平台台凭借其独特的彩票玩法和创新的哈希算法,公平公正-方便快捷!哈希游戏官网,哈希游戏平台,哈希娱乐,哈希游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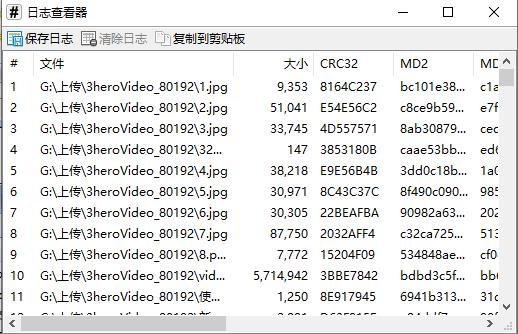
鹰角网络联合创始人海猫络合物、 thatgamecompany CEO兼首席创意官陈星汉、机核网创始人西蒙共同探讨了独立游戏开发者可能面临的困难与迷茫,海猫络合物与陈星汉从个人经历出发介绍了自己在游戏开发过程中得到的帮助。
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能主持这个圆桌,仿佛回到机核录了一期专题节目一样。我们三个的身份可能不是特别一样:海猫老师和陈星汉老师是游戏开发者,我则是在机核经营内容社区,但是我们三家公司在之前合作了一个游戏开发的活动,所以其实也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未来可能为早期独立游戏及开发者提供支持。
今天我们主要会聊中国早期的游戏开发的生态,包括从0到1的开发这部分的内容。那么想先问问海猫,开拓芯成立至今也有几年的时间了,你怎么看待目前国内独立游戏开发的生态?
其实我自己入行的时候,国内的独立游戏还比较少,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独立游戏在国外其实也算是萌芽状态。我记得当时是《以撒的结合》(The Binding of Isaac)刚推出的时候,它属于国外第一代比较典型的独立开发游戏,是正式进入了大众视野的状态。然后那几年内,整个独立游戏在国内的发展是非常迅猛的,无论是开发者的数量,还是游戏市场的整体发展情况,势头都非常迅猛。
在开发者数量方面,希望大家注意一个事情,就是游戏的出现和游戏开发者的出现就像浪潮一样、并不完全同步,是先有开发者,然后他们在几年之后把游戏做了出来,游戏才出现。事实上,现在你能看到的游戏的迅猛势头,其实是之前更迅猛的开发者势头的出现造成的。现在隐藏在浪潮之下还在努力的开发者,包括在座的诸位,都是未来独立开发者的苗子,大家未来都能够做出不错的作品。
我也分享一个我的感受,机核之前一直在做核聚变游戏嘉年华的活动,基本上我们每年会到三个城市办展会。到目前为止,我们可能已经和上千个开发团队交流过,发现很多早期的游戏开发者很缺乏信息或者是资源,包括钱、平台等。但在整个商业链条里,投资人和发行商往往都会在游戏有了成熟Demo,或者说有了团队、甚至有了公司之后,才会进入到这个流程里面。在游戏开发的前期,开发者一直是比较缺乏支持的。我想问问陈星汉老师,比如说前面的十年,海外开发者们是会在独立游戏社区里面自发去进行游戏开发,还是有机构会对他们进行扶持?
我们开始做独立游戏是2005年开始。2005年的时候没有iOS平台,也没有Steam平台,所以当时的独立游戏环境是非常狭小的,游戏平台只有任天堂、索尼和Xbox,只有在他们愿意支持的情况下,才可以让一个小游戏去卖一个盒装实体版。
你要卖一个游戏的话,必须要去实体店。那时卖游戏就像卖一本书一样,绝大多数的游戏都是我们说的3A游戏,卖60美元,是很贵的。如果你拿过来一个只收10美元的游戏,商店老板都不愿意把它放上去。当时是一个完全被渠道控制的发行环境。
一款商店里卖60美元的游戏,可能40美元都是被中间各个渠道分销商拿走,所以人们不愿意在商店里放一个便宜的游戏。后来主要还是靠数字下载的平台,让开发者可以更便宜地把一个游戏放到货架上。
对,我们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做独立游戏的。但是一开始Xbox和索尼不敢把服务放开给所有人,它还要去审核每一个开发商的游戏作品,这些作品要达到一定的完成度才可以上线年之前的独立游戏,我可以说全世界每一个独立开发者我都认识。但是现在开发者太多了,每一个人都是游戏开发者了。所以我觉得,我是那个时代的恐龙。后面经历了Steam的革新,再到现在的手机游戏,游戏的革新彻底地让开发的门槛降到了最低。所以我一直跟别人说,现在是独立游戏的文艺复兴时期。
文艺复兴发生在黑死病之后,这时欧洲三分之二的人都死了,剩下来的三分之一的人有很多的资源,不用再去竞争资源,他们就开始去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于是就出现了很多新的思想。这一时期很像诸子百家的那个年代。其实,如果我们从独立游戏的角度去看的话,现在几乎每个月、每两个星期,就有一个新的爆款游戏。这个在过去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真的是独立游戏的黄金时代。
我觉得现在“独立游戏”的意义比较宽泛了。以往大家定义独立游戏的时候可能指的是不能拿到投资,或者是不能以公司为主体。但是我觉得这样限制有点大,而且投资的方式也是越来越丰富的。
我认为以玩家的视角来说,独立游戏应该是风格独特的,其中有一些由作者提供的、个人的色彩就行。可能有些是表达方式上很文艺,也有一些是玩法很独特。比如《小丑牌》(Balatro),这种游戏就是好玩、上瘾,它看上去非常灵巧、敏捷,然后风格相对非常独特,让你感到它不是打磨到非常圆滑没有特色的东西。独立游戏必须有特色——这个是我认为一个很关键的点。此外,规模很大那肯定也不能叫独立游戏了,千人开发的游戏很难叫独立游戏。我觉得独立游戏怎么说也应该有一个开发者人数的限制,可能50人左右的开发团队已经算很大很大了。我认为如果有这一开发规模的、个性非常鲜明的游戏,大概就能算一个广泛意义上的独立游戏。
因为当年我们刚开始开发游戏的时候,索尼发行了我们的游戏。就有很多人说,你们根本就不是独立游戏公司,你们用的是索尼的钱。我说我们才四个人,怎么不是独立游戏公司呢?所以我一直要跟别人辩护,说我们是独立游戏制作者。
之后我们一直在思考,到底什么样的游戏才算是独立游戏。其实我们内定义的:它是一个目前为止在商业上尚未被证明是成功的游戏。比如说Mojang, 他们做《我的世界》(Minecraft)的时候,这一类型的游戏的确从来没有被证明过,那么它可以是一个独立游戏。但是《我的世界》成功了以后,所有的沙盒游戏在我来看可能已经不是很独立了。
也就是说,某一类型的游戏已经被商业验证之后,这一类型的游戏可能就都不算那么独立了。
就像《我的世界》成功了,大家就会千军万马地去做沙盒游戏的变种,对吧?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它的独立精神就没有那么强烈了。我觉得在独立游戏领域,我们要奖励的是开疆拓土的创作者,像“开拓芯”的意思一样。我以前有个导师叫Will Wright,他是做虚拟城市和虚拟人生这一类游戏的。他认为,所谓的开疆拓土,就像一开始欧洲的殖民者到了美洲大陆,会先建立纽约、费城这样一些城市。在两个城市中间发现一个新的有资源的地方,就再去建一个城市。但这种东西在我看来,叫做两个游戏类型的混合体。比如有人发现了一个射击游戏,有人发现了一个动作游戏,有人会把两个游戏合体、找出一个动作射击游戏。但在Will的定义中,这不叫开疆扩土,这只是在已有的范围内找到了混合体。真正的开疆扩土是去发现一些过去根本不存在的游戏内容。所以我们一直觉得如果是独立游戏,就要有这种开拓的精神。
现在我觉得有个现状:游戏类型的版图有点开得太广了,已经开始挑战人脑的极限了。所以我觉得确实也可以这么定义独立游戏,但可能以现在的游戏开发来说,这个要求也很苛刻了。这样的游戏应该可以说是那种顶尖的、极具独立精神的游戏。但很多独立游戏的话,可能有着各自的表达,不一定要往“开疆拓土”的方向走。独立游戏肯定需要有探索,但可能每个游戏的开拓的“度”和开拓的领域略有不同。我觉得这种有探索的游戏也可以定义为广泛的、有独立精神的游戏。
前面你提到,独立游戏有很强烈的个人的声音,我也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大家都只开发我们认为别人喜欢玩的游戏的话,那么就会出现很同质的现象。而追求自己想要说什么的声音,反而会让我们创造出各种不同的维度。
我的背景是学电影,我们看电影史上一般都是做独立电影的导演会追逐自己的声音,比如希区柯克或者大卫·林奇。他们刚开始做电影的时候,别人都会说,这是什么东西,怪怪的,对吧?但是当这些导演找到很多观众之后,他们就成了一个流派。每一个人的品味都是不一样的,在美国,有一个游戏发行公司叫Annapurna,他们在选择游戏时有一个口号,就是要支持“深度的、个人的”游戏。这样才可能找到新的东西。
刚才我们讨论了独立游戏的定义,我觉得在当下,不管是Steam的覆盖面还是手机平台的兴起,都让很多人可以从事到游戏领域之中。我觉得大家对于创意的追求肯定不一样,但是其实都面临着同样的、很现实的问题,比如说资源,比如说早期的钱等等。二位从业时间其实都很久了,那我也想问问,二位作为早期的独立开发者,在你们最开始开发游戏的时候给过你们最重要帮助的人或者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首先经验是比较重要的。做独立游戏的话,大家会经历很多事情、扮演很多角色。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人我会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同伴,一个是外部的帮助。同伴是很关键的,我一直把鹰角网络目前取得的成绩归功于我们的创始人和早期同伴,以及后面很多的核心成员的不断努力。他们对整个公司的方向、文化、调性发挥了奠基作用,使得公司能一直往下走。
当然,外部的帮助也是非常关键的。我在刚进入游戏行业的时候有另一份工作,当时公司比较缺人,我本身是一个做美术的,结果在项目内扮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比如说PM,还做一些设定、甚至是程序上的工作。当然我不会写程序,但是我得学Unity,自己摆UI,以及研究一些压缩格式之类有的没的,这样探索下来之后好像什么都学到了一点。包括作为被投这种角色以及跟发行沟通这些事情上,接触了很多此前完全不知道的信息。也许对这些领域不精通,但是至少有了基本的知识。
早期的合作经历让我建立起一种认知:作为研发方,我们与发行方拥有各自不同的诉求,但我们能够共同做成一件事。这也让我们开始思考:如何选择合适的发行伙伴?什么样的发行商才是优质的?在我后来创立鹰角网络的过程中,这些认知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我也有了一些新的收获。
所以我认为对于各位开发者而言,在项目前期,大家的知识主要集中在研发领域。但在怎么进行发行、销售以及如何与外部伙伴沟通的方面往往存在知识上的不足。包括在公司的长期发展中,如何合理运用资金以确保游戏的顺利产出,也是需要持续学习的事情。这些领域能力的提升,往往需要一定的机遇以及那些能够提供宝贵建议的“贵人”的帮助。然后在汲取这些经验后也要学会融会贯通,这样才能助力你在游戏开发的路上走得更远一些。
我的经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在其他公司任职,二是创立自己的公司。自己去做这个事情时就要接触很多很多事情,可以说是在一路摸索: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吃了亏就吸取教训、及时调整,然后继续前行。
以我们的《明日方舟》为例,游戏在三测后遇到了一些情况。当时,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沿用了行业通行的做法,就是说,“诶!别家也是这么做的”,我们可以把条件调得更好一些,但结果还是引发了一些争议。后来我们仔细想,意识到市场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所面对的用户群体其实已经不同了。
当我们设计一款游戏时,初衷可能是面向特定的核心用户,比如A同学,但最终吸引来的可能是更广泛的用户群体,可能A、B、C、D、E都来了。这当然是好事,但随之而来的是B、C、D、E等不同用户群体截然不同的需求。此时就会面临新的选择:是否需要调整产品来满足这些新的需求?我的观点是可以进行选择,如果你决定专注于服务最初的核心用户A同学,那就坚持做好这一点;但如果你希望尝试将游戏推向更广阔的受众,那就需要广泛吸纳各方意见,在优化产品的同时,也必须确保像A同学这样的核心用户的体验不受影响。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的选择会让你走上不同的道路。
说到具体的人,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研究生导师 Tracy Follett。当时我们没有想到要做和别人不一样的游戏,基本上是海外什么游戏火,我们就借鉴什么。到了美国读研时,我需要完成毕业设计项目,我最初的构思也是借鉴《模拟城市》这类游戏。这时,我的导师问了我一句关键的话:“你这个游戏有主角吗?”我说,我没想过主角,《模拟城市》要什么主角啊?接着她提出了一个建议:“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主角是一个小孩?”
当时我的感觉就像是接到了导师的“命令”:毕业生导师命令我的主角一定是个小孩。作为一个大学生,我不会去想一个小孩子在想什么东西。但正是这个“要求”,让我意识到我可以追溯自己的童年记忆,并尝试将这些记忆融入到游戏中。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回忆打动了许多玩家,不少人玩哭了,甚至写信鼓励我:“你一定要创业,去做能打动人心的游戏!”那个时候是2005年,其实没有什么游戏是能够让人掉眼泪的。正是我老师的这个强制性的要求,让我走上了文艺游戏路线。没有她,我可能已经不在游戏行业了,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关键贵人。
第二位至关重要的人,是给予我们第一笔资金支持的投资人。那时我们四处融资,环境非常艰难,市场上几乎没有VC关注游戏行业。而且整个游戏行业曾经历过一场“灾难”,有个游戏叫《E.T.外星人》(E.T. the Extra-Terrestrial),它最后被看成是雅达利大崩溃的开端。这个事件把整个游戏行业埋进了坑里,从那以后大家都不敢投资,觉得游戏行业风险性太大,所以只能够靠发行商。
当时我特别感激索尼发行部门的John Hight,他后来成了《魔兽世界》的制作人。在索尼时,他管理的就是数字下载平台PlayStation。当时我给他介绍我们的游戏《云》——其实就是《光·遇》的前身。他说,我可以理解你这个游戏为什么有很多人会喜欢,但是我现在不能证明你这个市场的能力,但是你的毕业生作品——我当时做的另外一个游戏《Flow》(流)——那个游戏我可以发。当时,我一直在跟所有的发行商推荐我们的《云》,但是没有人敢接。
对。2006 年的时候我在跟Steam谈:“你能发行我这个游戏吗?”Steam那个时候还没有独立的游戏平台,他们认为:“我们所有的游戏都是打枪的,你这里面又没有枪,我们为什么要发行你的游戏?”这就是他们的原话。
对。Steam那个时候算是个独立游戏公司,对吧?他们也是想说,我们能帮到你吗?我们帮不到你,因为我们玩家只喜欢打枪。所以当时索尼的John Hight,他居然愿意接受我们这样一个都是在校学生组成的公司。我们从一个只是在学校做游戏的团队,变成了一个在商业的游戏平台上推出游戏的公司。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们团队就说,我们做的游戏能够被PlayStation发出来、让所有人都可以玩到,就算不给我们钱,我们都是愿意做的。
是的。所以这位让我们公司成立的人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再下一步的话,就是我们做完三个PlayStation游戏之后,我们发现索尼发行的商务合同,其实是对我们非常不利的。我们是2006年完成签约的,推出《Journey》(风之旅人)时已经是2012年了,但还是当时那个学生契约,所以我们就觉得特别不公平。
不然的话,我们也没有机会去证明我们的能力,对吧?所以这都是公平的。最后从索尼离开之后,我们就去寻找风险投资。给我们投风险投资第一轮的投资人是Mitch Lasky,他也投了Riot Games(拳头游戏公司)。当时我们谈了很多很多风险投资人,但是没有人愿意投我们。我是礼拜五去见了Mitch,上午给他做了一个Pitch,下午他就追出来告诉我,你先别走,我们直接签约。下周一我就签了约——就是这么快。如果他不相信我们的话,我们就不会有《光·遇》。
我想,在座的各位听了两位的故事,肯定也希望从中获得启发——作为新入行者,是否也能像你们一样遇到关键的“贵人”?对于现在的开发者来说,哪些资源是最为重要的?这些关键角色通常会在什么阶段出现?以及,开发者们该如何主动争取到这样的机会?希望两位能再为我们分享一些见解。
我认为,这些情况最后可以说得更加直白:你想做个游戏,但是你没有资源和钱,对吧?有钱的话,你就可以置换不同的资源,那么一开始是谁给你提供第一笔资金?是你自己工作存下一笔钱供自己去做独立游戏?还是一个发行商或者是一个投资人为你提供资金?
我毕业的时候是没有投资人、也没有工作,所以我只能靠发行商。很多我们的同学会说那个时候还算幸运,刚刚赶上数字下载平台推出,我们现在没机会了,千军万马都要上Steam平台。其实资源是随着时间会变化的,有一段时间,微软推出了Kinect,当时他们特别需要人去做Kinect的内容,所以有很多的资源,很多人就是从微软那拿到资金,去做Kinect的游戏。后来还有VR,推出之后就有很多人会去做VR游戏。 其实我总觉得,资源永远会来,也总是会随着时间变化。核心就是能不能找到一个机遇,让你从一开始没有团队、没有资源的状态,到可以建立一个团队、把一个游戏做出来。国外有一个话就是“Youre only as good as your last game(你的价值仅等同于你最新作品的价值)”。别人看你,都是看你上一个发行的游戏是怎么样,所以你只要做出第一个游戏,就已经很不一样了。
正如陈老师所言,资源确实很关键。不过我觉得在获取资源之前,我们可以去主动学习,了解潜在资源的获取途径。以开拓芯为例,我们所做的不仅涉及投资商,大家也看到了,仅就今天的活动而言,它本身就是一个信息交换的机会。我认为它不仅提供信息,更提供了一个汇聚各类同学的场所——有的同学可能掌握某类信息,有的同学则拥有不同的资源,彼此间的交流可以实现信息互补。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上一份工作让我学会了如何获取信息。而在创立鹰角网络时,我就会去演练、去思考,我是否能从那边获得信息、如何获得信息,在这一过程中真刀真枪地完成实践。大家或许需要带着这种主动获取信息的意识去行动。
而开拓芯本身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我们广泛接触大家,就算最终不会进入投资环节——因为进入具体业务阶段,情况会变得复杂,未必有合适的合作机会,或者彼此的诉求可能不尽相同,这都难以强求——但我们始终非常乐意提供信息。事实上,大家需要的正是一本关于“如何做游戏”的新手手册。
从单一专业人士角度得到信息有时候会比较片面,比方说,开发商会说你加入我们公司就可以,发行商会说你把游戏发给我们就行,他们给到的建议不一定很全面。
而开拓芯目前是一个比较灵活的状态。我们没有必要说投了你以后才会给你信息,我们是很乐意去提供各种信息的。如果你遇到了我们愿意帮你解决的问题,那你可以来向我们寻求帮助。比如说不知道怎么开公司,不知道该找什么样的同伴;或者只有自己一个人,该怎么做一个独立游戏?此外,如果你想要针对海外市场或者国内某种特定文化,在涉及具体的发行策略上,也许我们有认识的同学会专门对这类游戏发行感兴趣。我们就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牵线搭桥的工作。
简单来说,我希望开拓芯能够扮演一个类似“资源黄页”或者“新手手册”的角色。当然我认为目前业界中还有很多人也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只是可能没有到台前来。我觉得关键是大家需要去广泛交流。
我觉得有人支持、讨论和塑造讨论的氛围是社区存在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大家必须要聊起来、实现信息互通,其实就像海猫你刚才说的一样,你正在扮演一个类似在你刚创业时遇到的贵人。
其实很多人可能并没有给我提供实质性的、具体的帮助,但是我仍然很感谢他们,因为他们会直白地告诉我:“这次虽然我帮不了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在哪里能找到方向”,或者说能够给我一些意见。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开拓芯的现场,让我想到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每年GDC(游戏开发者大会)的独立游戏展区。我基本上每年就只会去那里,我觉得在那里才可以看到游戏的未来,可以看到很多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们会有不同的想法。
我自己以前也在独立展区去展出我们的游戏。我觉得很多最重要的信息其实是从展台同桌那里学到的。有的时候你会遇到另外一个游戏的制作人,然后一拍即合、两个人决定一块做游戏。我们公司的1号程序员,就是在一个展会上碰到的。还有很多发行商、投资人也会来展会,我觉得这里是所有信息最密集的地方。
而且这些活动会比较垂直。有些时候活动不一定要做得很大,一个活动包罗万象之后可能来的人会变得五花八门的,他们之中差距很大,很多人可能只是看看。但像开拓芯这种活动可能定位会比较精确一些:我们注重新团队和独立团队。至少在整个商业版图上,独立游戏这个类型还是相对一致的,大家可能更容易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
刚才我们交流了创业早期的故事,但现在我觉得二位的身份又变了,现在无论是海猫的鹰角还是开拓芯,包括陈老师的thatgamecompany,都有新的、和独立游戏开发者相关的一些计划。从创业者变成了支持者,你们有什么感受?此外,还想要问海猫,是怎么考虑开拓芯的长期可持续化的部分?
首先,我回答感受的问题,因为答案比较简短。我认为做这件事情的感受就是很幸福、快乐。我自己的性格也如此,我们公司里很多同学的性格和公司文化也是如此。因为我们曾经寻求过帮助,也有很多人帮助过我们。所以我们觉得无论如何都想做一下。
这也不能说我们是完全地付出而不计回报,这个事情其实是在长期耕耘,很多时候你的无私贡献,实际上在未来有一天会回过头帮助你。这就是一种生态搭建。就像在足球赛事中青训这一步很关键一样,想要让好的独立游戏出现,就需要去耕耘,要对于游戏制作者们的生根发芽要有耐心,而且要有数量众多的人一起在做事情。如果说,一个城市里面只有10个人在踢足球,那么就很难选出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但是如果一个城里有1万人踢球,那你要选出10个优秀的人就比较简单,可以选出一个优秀的队伍,也可以有乙级队伍、丙级队伍,或者是大家经常提起的村超也会一样精彩。只有你的基数足够庞大、土壤足够坚实,大家都从底层开始、土壤级地去喜爱这项运动,喜爱这个文化,喜爱这个行业,那么未来才能出现顶尖的东西或是团队。这些顶尖的团队能够再去帮助其他人的话,才能够形成循环。所以,我觉得生态搭建比较关键。
我们现在也在做类似的事情。我们不能只着眼于“我投资你了、我才帮你”,而是要鼓励更多人、更多开发商加入进来。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发现:我们才到哪呢?业界有很多人都在做跟我们一样的事情,只是他们没有被大家知道。现在有开拓芯这样一个场合,希望能够把有志之士号召到一起来。未来可能再过五年、十年,游戏开发者和环境会越来越好,就可能有更多的玩家会接触到游戏行业,大家可能也会有多重身份:有些人是开发者,有些人是游戏玩家。大家也会对游戏有更多的了解、能够提供更多帮助。
今天听到海猫说的话,让我觉得很尊重,在你还看不到未来有什么回报的情况下,就愿意去帮助大家,这是非常无私的。当然我也相信付出一定会有回报。我有时候就在想:为什么人会做一件事情,但不追求回报?那么肯定是看到了一个更高的东西,比如说中国游戏产业,或者游戏在社会上被大家认知的地位——我们会去想一些更大的目标。我有的时候也会去帮助独立开发者,给他们提供建议和人脉。因为我觉得他们在做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了我的一个梦想,他们的游戏会帮助到游戏产业,那么我就愿意去提供帮助。
我在想,所有热爱游戏的人都会希望在未来某一刻,游戏在中国能够得到更多的尊重,游戏产业的开发者、游戏从业人员能够被身边的人尊重,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一个价值观。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些事。
是的。我们 10 年前创业的时候,大家看待游戏还是非常负面的。但是我觉得经历这十年的发展,中国游戏已经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了,而且又有新的平台的支持,我也相信未来的十年肯定会更好。
我还很好奇,现在机核和开拓芯都在支持开发者,我有的时候在想,我们是应该更广阔地在各地做各自的活动,还是要组成一个像海外的GDC一样更加综合的、覆盖更广的活动,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我们的活动之间都是在融合的。其实这也是我想问陈老师的问题,我觉得美国的游戏行业,我觉得他们这部分的协同可能更加紧密。中国经济发展迅猛,技术力提高了、门槛降低了,游戏行业发展得很好。但是我总觉得大家还在奔波于自己的事情,还没有一个特别的角色把东西整合到一起、把资源全部分享出来。我觉得这两年开拓芯也好、我们自己做的BOOOM也好,其实都已经在开始探索这些事情了,但是未来如果这些资源能够放在一起肯定会更好。
我觉得今年中国游戏发展这么迅猛,除了客观经济条件的变化以外,并没有什么事情是像超新星爆发一样突然出现的,都是一点点积累的结果。针对这个问题,我认为就是大的联动可以做,各自为战也可以做,有什么做什么,尽力而为就好。就像我们做开拓芯一样,我觉得关键的是要立足当下、脚踏实地:我可以根据现在的能力做一点事,等我以后变强了再做更多。 当游戏行业里面有很多游戏以后,玩家也会被吸引过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和游戏领域会被慢慢地塑造。只要持之以恒,我认为一定会有源源不断的开发者加入其中。
即使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可能看到了一些产品的失败,依然能够抱着“不计较成败、重在尝试”的心态投身于游戏开发的领域。此外,我认为游戏开发是一件就算失败了也很有意义的事情。无论如何,只要开发了就会提供一个作品。再差的游戏也几乎没有好评率为0%的,至少有那么一些人,他玩到了这个游戏并从中得到了乐趣,那么这个作品就是有贡献的。这样的贡献不容忽视,整个行业的繁荣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累积起来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用更耐心、更长远角度去看游戏开发这件事,无论你是开发者、投资者,只要怀揣着“尽力而为”的态度、积极投入资源就好,大家可以一起有耐心地向更远、更好的目标去努力。
海猫说的内容我也深有体会,我觉得做平台这种事情也很难。游戏它有版本、有节点,经营公司有一年的、两年的目标,但有时候平台是需要持之以恒的,你只有坚持,它才有火花。平台像一个有可能性的、有缘分的池塘,如果水干涸了,池塘可能就没了;但是只要能让水一直在这流,我觉得未来就会有特别好的东西出现。所以有时候,目标也不是一个在任何事情上都能体现特别完美的东西。我很认可海猫说的,你需要有耐心、长期地投入其中,你可能没法期盼今年有什么或者明年有什么成果,但是我觉得未来就是在这样慢慢做的过程中产生的。
我们希望能够把开拓芯提供给各位开发者的帮助做得更加全面、具体一些,扮演好我们作为“扶持者”的这样一个角色。然后,大家也能够看到我们今年的活动已经有比较大的突破,我们找了很多海内外的发行商、开发商,将他们介绍给到国内来和各位做交流。总之,我们会往沿这个道路继续推进。然后也希望以往我们投资过、帮助过的项目能够生根发芽。我们也非常欣慰其中已经有很多项目能够成功发售了。
未来的话,我希望开拓芯能够做得更大,能够覆盖到、帮助到更多同学,把我们独立游戏开发者的声量做得更大一些,吸引更多人参与到实践之中。走出第一步很关键,我们还是希望更多人能够发出人生中第一款、甚至是第二款游戏。这个事也很重要,也很难。
其实在做《光·遇》之前,我们是一家非常小的、几乎要破产的独立游戏公司,当时也帮不到国内的游戏开发者。我记得在2012年左右,我回了一次国,很多美院的学生、独立游戏制作人,他们会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帮到我们,或者问是否可以来我的公司求职。我说我们自己没有资金,还雇不了人,帮不到你,我唯一可以帮到你们的就是和你们分享一些我们做游戏的经验。 感谢《光·遇》过去这么多年的在商业上的成功,让我们现在有了一些积累,所以我们真的现在可以在资金、制作或者在发行上面提供帮助,我们也积累了一个团队。所以现在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TGC(thatgamecompany)的能力帮助到国内的独立游戏开发者们——如果我们的游戏类型和你想做的类型是有一些相似的,那我们的经验就会对你非常有用。我们也在学习游戏发行,包括如何在全球发行手机游戏以及发行PC游戏。如果能在国内找到与我们志同道合的人,我们可以提供相关的帮助。
我也想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动。机核这些年在做“BOOOM暴造”这个孵化品牌,也得到了鹰角的支持。之前我们一直是借助机核的核聚变、以及线上的社区,引导一些玩家更多地参与到游戏前期的测试和反馈之中。我觉得很多开发者也通过我们的活动跟用户近距离地接触,这个也是开发者早期最重要的一个得到反馈的机制,能让他们更有动力去继续开发游戏。我们今年有一些变化,下半年我们跟朝阳区合作、成立了位于北京的一个孵化器,如果是有同学在北方的话,也可以来找我们获得一些早期的支持和帮助。
